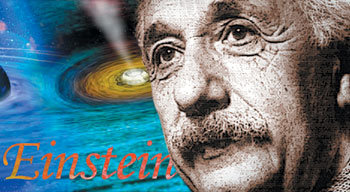
迄今爲止,我們認爲有負於他的是對他的“宇宙觀”的態度。但是他在該書中描寫的是自己的“世界觀(weltbild)”。
在該書中,讀者可以瞭解到一生致力於物質和能源、光速和時間等研究的科學家向人們展示的實踐性智慧。該書是從寄稿和演講中篩選的一位元科學家的“參與記錄”。他的文筆樸素,但很執著。其抨擊的物件之一是對以狂熱和破壞譜寫現代史,並威脅了個人的和平和珍貴的“集體主義”。
在讀該書的內容之前,可以想象到哲學家奧爾特加•加塞特在《大衆的叛逆》中所提出的問題,即,爲什麽致力於研究“小小專業領域”的科學家談論社會倫理問題?賦予他這種權威是否妥當?
雖然並沒有對他的問題做出直接回答,但愛因斯坦是這樣說的,“在感到保持沈默就像是共犯時,我一直提出自己小小的意見。”他在書中經常提到“智慧及倫理性作業”也意味著他從世界倫理性認識到一個科學家的職責所在。
他的世界觀通過個人面向國際政治和人類各個領域。即,人生的目標是什麽?在他人身上索取更多東西並不是能力所在。只有奉獻,才能決定人類的價值。我的生活來自於其他人的辛勞,所以應把這一切奉獻給他人,這應該成爲生活的目標。
他所說的“他人”之中,排他性共同體和集體無立足之地。所擁有的就是個人和整體,即,人類共同體。“只有個人才能私有,只有個人,才擁有靈魂”。從這句話中可以想象到說出“聖靈始終降臨在某一個人身上。”(《基拉雷薩的屠殺》)的Constantin Virgil Gheorghiu的名言。
他對“個人”的關心,直接聯繫到“體制”。“如果人類把一切浪費在籌集每天的生活必須品上,那麽其他方式的自由也就成了無用之物。”“資本主義無休止的競爭存在有可能麻痹個人社會意識的危險。”由於他提出了這種觀點,所以在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狂潮中,處在了被打倒的威脅之中。當時的真相在最近發行的《愛因斯坦文件》(EJ BOOKS出版社)中描寫得十分透徹。
但是針對個人,他的情緒與專制主義不能融爲一體是理所當然的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開始,同時平等地批判了法西斯主義和布林斯維克主義對人類的欺壓。“社會主義把不屬於自己一方的人全部歸類爲‘惡人’。”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並沒有忘記計劃經濟“將使個人成爲奴隸”。
戰爭結束後,強調孤立無援的人類之珍貴的物理學在全世界的尊重和嘲笑中,開始進入“宣言”階段。美國、蘇聯、英國等3國要求建立相互合作的“世界政府”。即,爲世界安全把所有軍隊整編爲多國部隊,並重新部署。
“爲防止出現萬人對萬人的鬥爭,個別國家只能犧牲自主權。”但是針對這一提議世界各國的反應十分冷淡,尤其是蘇維埃的反應。所謂世界政府就是企圖把投資領域擴大到全世界的資本家的陰謀。他的理論是不是過於超前?
1952年他被提名當選新成立的以色列首任總統時,一口拒絕也在情理之中。對他而言,所謂猶太人“民族國家”無疑是把從“民族主義”所遭受的痛苦反過來強加給全世界。
今年是該書原版出版第50個年頭。與他同時代的作家斯蒂芬•茨威格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稱爲“瞬間嘗試從進步的天堂到地獄以及人類逐步發展歷史的時代。”一個時代的痛苦造就了一個時代的智慧,但是世界的文明保持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,人類正在逐漸忘記對自身破壞本性的警示。利用“個人”及“全人類”,呼籲和平的科學家的啓示至今仍感到新穎,也許也正緣於此。
劉潤鐘 gustav@donga.com







